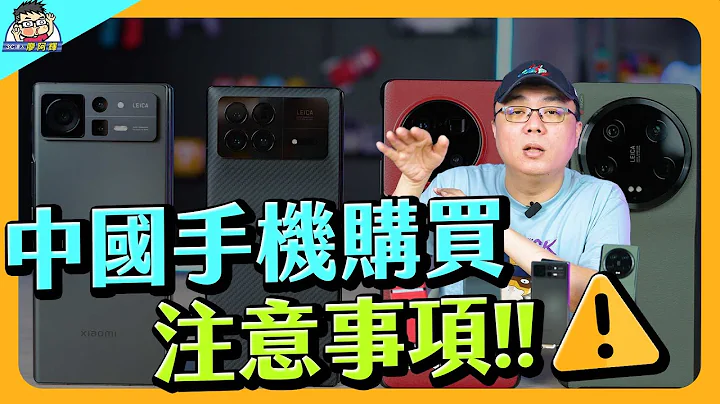購得飛利浦電子管CD機一台,尋尋覓覓很久,不能像丁元英那樣玩硬件,只能用套機,挑來挑去,遇到了這台飛利浦。它本就是老牌音響,這台機器的前級用了捷克軍工電子管,後級仍是數字功放,這樣的組合真是很巧,有着1+1大於2的效果,於是果斷入手。開機後,電子管預熱10秒,看着那閃閃的紅光,好懷舊的感覺。

手上有幾套電子管錄音的CD,喜歡那淳樸原始的音質,現在又有了膽機,就更配了。音質乾淨圓潤,音量開大也不會有震耳欲聾的感覺,聽FM時會變得很強大,低音炮的感覺來了,嗡嗡的。更喜歡CD播放的聲音,溫柔通透聲聲入耳,很舒服自在的感覺。終於有了能令自己滿意的機器。

音樂發燒友中有很多玩硬件的,我不是發燒友,也玩不起硬件,有一個攝影已經夠了,如果攝影和音響一起玩,家會被敗光的。如今有了心愛的CD膽機,也收藏了幾張有價值的黑膠,滿足之餘又想起一個聽音樂的經歷。
幾年前春寒料峭之時,朋友帶我去一個詩社聽黑膠。詩社主編是一位老漢兒,自稱農民,顏值大約是《白鹿原》里白嘉軒那樣的農民。雖稱不上儒雅,但也一定是個有趣味的人。他先是讓我隨意翻看架上的書籍,之後便帶我進入他的聽音室。

老漢也有自己的一間公司,把掙的錢投到了聽黑膠上。他專門為自己安排了一間聽音室,功放、音箱、大屏一應俱全且檔位甚高,還有專門存放黑膠的房間。我想找一張莫扎特的21號鋼琴協奏曲,欣賞一下他的組合音響,老漢兒說沒有,只有《春江花夜月》這樣的,還有崑曲。老漢兒說他是個“臨川夢裡度餘生”的傢伙,酷愛崑曲。他給我看詩社的刊物,裡面還記載着他與我這位哥們兒一起打飛的去上海聽崑曲的經歷,以及他們沉浸在劇中如醉如痴的表情。
我喜歡青春版的《牡丹亭》,老漢兒則最喜歡單雯16歲時唱的“鼓舌如鶯黃”的那版,認為深得崑曲的真諦。所以先聽了單雯那版,之後又看了青春版的《驚夢》。我喜歡把不同版本的放在一起聽,老漢兒拿來了兩個版本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聽不同版本是很多音樂愛好者的一好,在這點上,我與老漢兒是共同的。我提到我一直沒找到《淡水小鎮》,老漢兒說“在這兒聽吧。”他拿出了《淡水小鎮》的黑膠,後來又拿出了鮑比達《關於愛情》的CD 和黑膠,鮑比達的鋼琴迴旋在幽暗的空間里,我們就這樣安靜地坐着,黑膠細細的沙沙聲是那麼柔美,它彷彿是一種朦朧的空間,包裹着我們的靈魂。
離開聽音室,我們一起去老漢兒熟悉的小館子喝酒,他不僅挑出了自己珍存的佳釀,還把詩社的刊物也帶上了。酒過三巡,老漢兒從刊中挑了他寫的《鷓鴣聲聲》套曲讓我念,看着這題目我心中一動,鷓鴣聲可是有着明確的含義指向的,這聲中含着些什麼呢?
果然,念了幾首我便指着一段詞句對老漢說,“這裡面有故事”。老漢兒微笑道:“都過去了。”我問:“能過去嗎?”他說:“能過去”,並微笑着點頭。真的過去了嗎?那為什麼還點名念這首詞?我望着那張微醺的臉,忽然覺得人老了真好,有那麼多積澱,有那麼多故事,有那麼多可以回首的往事。看着老漢兒臉上的微笑,那就是回首時的一種滿足吧?

本來是來見識音響聽黑膠的,沒想到還聽了鷓鴣聲聲。音樂總是能拓展人的思緒,令人的情感更細膩更飽滿。老漢兒說他是“臨川夢裡度餘生”,這不僅是對崑曲的喜愛,那些虛虛實實、真真假假、似有似無又刻骨銘心的夢境與真實,讓人如何忘得了?黑膠記錄的那些“臨川夢”,那細細的沙沙聲,伴着那些在人心不古、物慾橫流中仍堅守真淳情感的人們,在夢境與真實中不斷出入,淺吟低唱,始終保有自己的世界,這樣的餘生該有多美。回想這段往事,覺得我的飛利浦真好,我的CD架,我的黑膠箱真好,它們帶給我的不只是音樂,而是陪伴,是最好的陪伴,它們才是餘生不離不棄的伴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