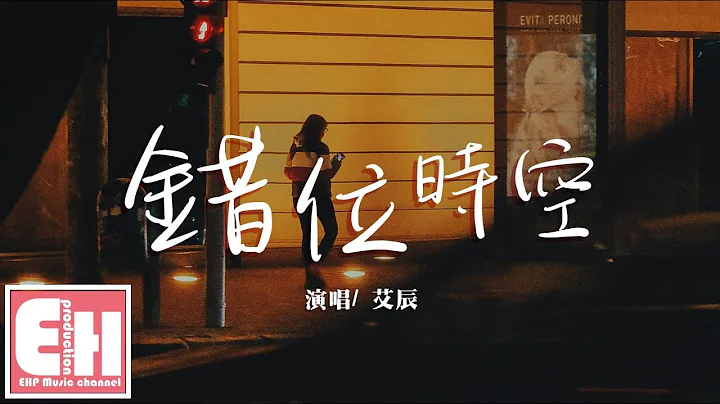2022年10月,應《報恩》所邀,攝影師王堅與雜誌編輯人員熱情分享了其在七塔寺拍攝多年的所見、所思、所感,以及作為一名資深攝影愛好者多年來對於攝影藝術的熱愛、堅守與期許。
人物介紹
王堅,寧波鄞州人,別署“覺路七塔”。秉持“無它,唯手熟爾”理念,悉心創作,堅持以攝影的方式讀懂一座寺院、一個城市。

葉偉 攝
從影介紹
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接觸攝影,師從洪柏春先生。90年代起開始攝影藝術創作,主要方向是風光題材,先後師從郭一清先生、李元先生。
2001年,獲“柯達杯”《中國攝影》2001年度專業反轉片優秀攝影師提名獎。
2001年,獲第八屆佳能杯“亞洲風采”華人攝影比賽人與自然類三等獎。
2002年,多幅作品入選《中國上海第六屆國際攝影藝術展覽》。
2002年,獲中國攝影家協會網首屆“影友拼圖”半月賽十佳作者獎。
2016年,個展“錢湖早安——王堅攝影作品展” 分別在中國攝影家協會寧波藝術中心、寧波市文化館開展,此次展覽共展出錢湖早安系列作品50餘幅。與此同時,個人攝影作品集——《錢湖早安》在葉偉先生的悉心製作下完成,一段甬城東錢湖歲月變遷的影像記錄史,由此誕生。
2016年,開始創作《覺路七塔》系列攝影作品,並為《報恩》雜誌和七塔禪寺、棲心圖書館等有關單位微信公眾平台提供圖片。
2020年,“棲心梵影——王堅攝影作品展”在七塔禪寺棲心圖書館舉辦,此次展覽精選了王堅在寺院拍攝創作的藝術佳品20餘幅,吸引了廣大甬城信眾、讀者及攝影愛好者觀展。展覽結束後,王堅將所有展品對外義賣,所得善款悉數贈與棲心圖書館。

“棲心梵影——王堅攝影作品展”部分展品
一、佛教題材攝影:七塔開覺路,光影傳正道
《報恩》:您在網絡上專門發布七塔寺相關攝影作品的賬號名為“覺路七塔”,背後有何寓意?
王堅:2016年12月25日,在整理七塔寺相關攝影作品以備後續出影集相關事宜時,可祥法師定調取名為“覺路七塔”。2017年,我在今日頭條號上分享七塔寺的攝影作品時,使用了這個名字。

可祥法師手書“覺路七塔”
李白《春日歸山寄孟浩然》中有詩句云:“金繩開覺路,寶筏度迷川”。這兩句詩的意思是佛法能開啟眾生覺悟的道路,超度眾生脫離迷惑,到達理想的彼岸世界。我對“覺路七塔”的理解:“覺路”即覺悟之路,要依照佛陀教導的“四聖諦”“六度”“八正道”等正法來修持,才能像佛一樣開大智慧,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“塔”是佛的象徵,所謂能如實覺知者為佛,“七塔”喻示過去七佛:毗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毗舍浮佛、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、釋迦牟尼佛,為禪宗法脈源頭表徵,七塔禪寺之“七塔”即為此意。“覺路七塔”的寓意是大家要依照佛法來修行,將攝影藝術、讀書作文等日常生活上升至修行的高度,最終目的都是要達到禪宗所言“明本心、見本性”,抵達覺悟之彼岸。
《報恩》:您使用賬號“覺路七塔”發布攝影作品之前,是否通過網絡分享過其他的作品?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開始在網絡上分享自己在七塔寺拍攝的圖片?
王堅:我以前有一個微信公眾號,叫“錢湖早安”,主要發布的是我在東錢湖拍攝的一些風光攝影作品。“覺路七塔”的頭條號現在有六千多的粉絲,這上面發布的基本上都是七塔寺的垂直內容,關注者主要是寧波本地人,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。
選擇在網絡上發布七塔寺的作品,目的有三:一是把佛教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現象來觀察研究,希望通過發布一些在七塔寺拍攝的照片,來增進大眾對於正統佛教文化的了解;二就是為了和更多人分享,有很多人一年到頭難得親自到寺院一趟,發布這些照片也能夠與他們共享寺院一年四季的風景;三是為了讓作品“試水”。對於那些我自己覺得有把握的照片,其實不發也可以,但那些介於“好”和“壞”之間的照片,自己把握不好,就會拿出來讓大家評論。有時候自己覺得滿意的作品反響不大,自己覺得平平的,反而有很好的反響,個人和大眾的取向還是存在一點區別的,攝影者本人需要傾聽更多的聲音。
《報恩》:您為七塔寺拍攝了豐富的攝影作品,包含大量的寺院建築、人物肖像、佛事活動現場圖等。作為老寧波人,您與七塔寺的淵源從何而起?
王堅:拍攝七塔寺之前,我一直拍攝的都是自然風光題材,到了2016年,《錢湖早安》影集出版後,我想更換拍攝對象和題材,也是為了挑戰一下自己。因緣際會之間,就有了開始的契機。
有朋友曾問我在七塔寺拍了這麼長時間,最大的感受是什麼?我說每次進到寺院里來,就感覺到家了,內心有一種平靜油然而生。
很難說清楚這種感覺,我一邁入寺院的大門,心裡就會感覺很舒服。以前連什麼是早課、晚課、過堂都不知道,隨着來的次數多起來,慢慢也就了解了。和師父們也變得熟悉起來。他們都對我很好,早上來的時候,會問我吃飯了沒?也聊聊今天的天氣如何等等,有時還會把他們早上分到的小點心、水果往我的包里塞。如果有一段時間沒來,再來的時候他們就會問“這段時間幹什麼去啦?怎麼沒來?”現在感覺他們像家人一樣,這個熟悉的過程就像手串慢慢包漿一樣,很有意思。
《報恩》:七塔寺影集的籌備目前進行得如何?您在籌備過程中有什麼感受?選入影集的作品有什麼標準?
王堅:最近一直在做七塔寺影集的籌備工作,主要是挑選、彙編和整理照片。從2016年到現在,我來七塔寺拍照的次數有六七百次,有時候早上來,有時候下午來,有時候早上、下午都會來,一年下來會有十萬張左右的照片。截止到現在,我拍攝了大概有五、六十萬張與七塔寺相關的照片,這個體量實在太大。
我會按時間順序將作品進行備份,現在就是從最早一直往後翻閱、整理和挑選。整理照片這件事做起來是“痛並快樂着”。“痛”是因為挑選照片很難,有時候選一天,一張好的照片都選不出來。現在進行第一道初篩,之後還要請人幫我再次梳理。如果不是自己的照片,可能就會更加理性地去做一些取捨,而自己拍攝的作品,卻有點難以下手,這感覺就跟外科醫生不敢給親人做手術一樣。
第一道篩選工作完成後,應該要選出四五千張,眼下大概進展到一半。目前我對於影集的想法是:大概挑選出五百張以內的照片,具體怎麼選要看整體的作品質量,要兼顧不同照片之間的協調性等,後續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商討。至於挑選作品的標準,首先是要自己覺得順眼;第二是要看符不符合寺院的風格;第三是看單個作品能不能融入影集的整體風格中,內部要有一個整體的平衡,主要就是這三點。
《報恩》:您以前拍攝自然風光較多,現在則以寺院題材為主,在創作不同題材的作品時,您會有意地使用不同的攝影技法嗎?您如何在作品中傳達佛教氣質和禪意?
王堅:不管是風光攝影還是寺院題材,技術原理都是一樣的。比如說,好的作品都要有好的光影效果,要抓住變化的瞬間。拍攝寺院題材影像,從原理上講,可以把房子看成山,把人看成樹木,技術上其實是差不多的。但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調整來凸顯寺院的氣質,佛教所特有的東西要藉助人、佛像、建築之間的結合來表現。
至於禪意,有的人說靜是禪,有的人說動是禪,這看個人的心境。
《報恩》:在您拍攝的大量作品中,是否有一二幅傾心之作?展開談談這些作品背後的意境?
王堅:讓我從作品裡挑出最滿意的,很難。因為每張照片都是自己親手創造出來的。不過我也挑了幾張自己比較滿意的,跟你們分享一下。

這張是一位老香客在上香時的場景。在寺院拍照,還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:信仰其實是很隱私的東西。創作者在拍攝的時候不僅要表現出香客的虔誠,同時又要保護個人的隱私,這對攝影師來說是責任,一定程度上也會增加拍攝的難度。像這張照片,很靜,人物的狀態也很虔誠,光線又好,肢體語言、心境還有環境結合在一起,很和諧。從審美的視角來看,光線包括煙霧的動態,都富有美感。

這張照片表現了佛像的莊嚴。佛像看上去很高大,鏡頭經過一點變形之後,好像對佛像更有了一種仰視的感覺,同時也表現出殿堂的莊嚴。這一張從佛教的視角來看,圖像有些變形,不是很正,但從藝術角度來分析的話,這個角度衝擊力會更大一點。
三聖殿的佛像其實是最難拍的,因為佛像跟建築的比例比較特殊,佛像小、房子大。到現在為止,好像還沒拍到自己很滿意的片子。人的眼睛跟鏡頭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樣的,眼睛可以做到“視而不見”,但鏡頭不行,它會把視角範圍內的東西全部拍進去。所以長期從事攝影的人的觀察,跟平常人的觀察會有一點區別。攝影的難度也在這裡,要知道不同鏡頭的特性,知道想表現什麼東西的時候要換什麼鏡頭,以及這個鏡頭拍攝出來的效果會是什麼樣的。
我平時常用的鏡頭有一個12毫米的廣角、一個10-18毫米的超廣角和一個70-240毫米的長焦。一般情況下,我一天之內只用同一個鏡頭,因為不同鏡頭的拍攝思路是不一樣的,這樣拍攝的思路就不會受到干擾。

這一張我印象也很深刻。這位老居士站起來有些吃力,或者說她已經不能正常地跪拜,於是她就坐在凳子上叩拜,非常虔誠。雖然年事已高,但她仍舊堅持到寺院來禮佛。

這樣的照片是等出來的。心裡預先想好在什麼位置、要拍什麼,就提前找好位置,然後等在那邊。這張照片是受佛經里的內容所啟發而嘗試的,佛教講求“不着相”,如《金剛經》云:“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,即非菩薩”。《金剛經》又云:“一切有為法,如夢幻泡影;如露亦如電,應作如是觀”,強調有為法之無常變幻,這樣極具畫面感的經句是可以通過攝影作品表現的。

這張片子首先是通過一個固定點,多個焦點連續拍攝(大概二十幾張),後期採用“景深合成”的方式製作而成,最終把佛像的莊嚴寶相表現出來。平時禮佛的人,可能不會從這個角度去看佛像,但我們搞攝影的,要用一種“非常”的視角來表現佛像,把它表現得越殊勝,就越引人讚歎。
《報恩》:影像作品是歷史變遷的見證,這些年來您為七塔寺留存了大量的圖像素材,在翻閱整理過去的作品時,看着影像中所呈現出的七塔寺的發展變化,您有什麼感受?
王堅:這幾年變化確實很大,這個城市越來越美、越來越整潔,身在其中的七塔寺在周邊的映襯下也越來越散發出獨特的魅力。七塔禪寺主辦的天台佛教學術研討會今年已經舉行到第六屆,浙東佛教高等研修班也開始第二期,棲心講壇則進行到第五十七期,同時還舉辦了“之江問道·法雨長施”七塔禪寺棲心佛學系列講座、都市生活禪等活動。棲心圖書館的讀者也越來越多,有時侯會一座難求。隨着“文化興寺”理念的提出,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七塔寺會跟這個城市一樣,越來越好、越來越美。
《報恩》:您曾經提出“創作者要把創作意圖準確地傳遞給觀眾,以引起觀眾的共鳴”,在拍攝寺院題材的作品時,您通常會有什麼想表達的意圖呢?
王堅:這其實是兩個問題。首先,在我看來寺院題材跟其他題材的作品,最大的區別在於拍攝者要堅持真實創作,真實是最主要的。“以真、善、實”為美。擺拍對我來講,是不允許的。
李元先生將自己的風光攝影喻為“自然攝影”,就是不允許有任何東西添加或者改變作品的原貌。我所理解的“自然攝影”理念是“攝影原教旨主義”,即講究存在的自然。佛教是講隨緣的,既然是佛教題材,那麼擺拍就不是隨緣,也是對佛教的不尊重,這是我為自己劃的一道紅線。我的照片裡邊有人物出現的,都不是擺拍。其實這樣拍攝的難度很大,很多時候都需要等待,等待人物出現。比如說我覺得這個位置、這個光線可以,我就會在那裡等,相當於是自己給自己製造麻煩。
至於想傳達的創作意圖,就是要把佛教的建築之美、造像之美、器物之美、儀軌之美、傳統之美等內容通過畫面傳達給觀眾,讓大家了解真正的佛教是什麼樣的。這是我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。希望通過這些“正”的佛教題材作品盡量傳達真實的、正統的理念給觀眾。
二、攝影創作者要守住真實的底線
《報恩》:關於攝影創作,您持有“創作者需要具備觀眾對其作品進行‘拷問’的覺悟”的觀點,這句話如何理解?
王堅:“拷問”就是觀眾的質疑、批評,或者說讓創作者難堪。這種情況對創作者來說,是需要保持平常心來面對的。要做好心理準備,因為觀眾不會過多考慮客觀環境因素,比如拍攝時的位置、光線等等,他們只看最後的成品,這是他們的權利。
另外還有一點,觀眾人數眾多,聰明人大有人在,因此創作者不能覺得人家不專業。以前白居易寫詩不是還要念給老太太聽,寫到她們能聽懂嗎?美沒有外行,是有共同標準的。
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,創作者要正確地對待觀眾的眼光和評論,任何時候觀眾都是對的。好的作品自然會引起觀眾的共鳴。當創作者個人的標準跟觀眾標準不一樣的時候,就需要處理一個命題:是要隨大流還是堅持自己的個性?這看個人的選擇。但只要選擇把作品拿出來,就必須要接受觀眾的考核。拿出來接受拷問和自我欣賞是兩回事。
《報恩》:您這些年來在工作之餘一直深耕攝影領域,是什麼驅動着您始終堅持攝影工作?攝影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、給您帶來了什麼?
王堅:攝影於我,雖然時間是業餘的,但態度是專業的,這是我對自己的評價。我是有專業精神的,《錢湖早安》系列拍攝了九年才集結出版,從2016年開始,我在七塔寺拍攝也到第七個年頭了。
攝影的驅動力其實很簡單,就是好玩,拍照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。開始拍攝前要做許多選擇,比如這段時間葉子開始黃了,就要選擇樹葉、顏色的題材,接下來要選擇到什麼地方去拍、具體什麼時間點去拍,以及拍攝時天氣怎麼樣、要帶什麼東西、坐什麼交通工具、跟誰一起去……拍攝回來後還要考慮選片要怎麼選。攝影就是這樣一層一層進行的,每一層都非常有樂趣,每個選擇的改變都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東西。選擇拍攝的時間,其實也意味着等待。夏天的時候我會想,等過幾個月我就可以拍紅葉了,會有一種期盼的心情。
對我來說,有攝影這樣一個相伴多年的愛好,是很幸運的事情。有時候我都會自我感動,感覺自己對攝影是終生不渝的。
攝影給我帶來了許多東西。第一個就是讓我的時間過得充實,攝影是很費時間的;第二個是攝影要求人不斷精進,要學好多東西。不管是風光攝影還是佛教題材攝影,到最後比拼的是每個人的審美,而不是快門、光圈這些入門時需要掌握的技術。一個人的美學境界決定了其攝影的境界,攝影也提高了我個人的美學修養。平時一群人出去玩,玩攝影的人和不玩攝影的人觀察的東西都不一樣。經常有人問,我們明明跟你一起去的,你從哪裡拍來的這些照片?這一點也很有意思。
《報恩》:時下短視頻發展蓬勃,在您看來,視頻與圖片兩種作品的形式有什麼區別?
王堅:我一般不拍視頻。視頻是一種新的傳播方式,肯定有它的先進性,比如更全面,可以把一件事情講清楚。視頻跟攝影其實是兩個獨立的門類,如果要說難度的話,我肯定是覺得攝影略高一些,因為攝影只能用一個畫面儘可能地將事情表達清楚,而視頻是通過連續的畫面。但是當下視頻是大家喜聞樂見的,它的傳播範圍應該要比攝影作品更加廣泛。
《報恩》:您表達過“色彩對於攝影師而言是危險的,掌聲越多、陷得越深、色彩越艷,容易迷失自我,忘卻初心”的看法,能否再具體闡釋一下您對攝影色彩乃至背後攝影技法的看法?您覺得維繫攝影藝術的特性,最重要的是什麼?
王堅:這裡所說的“色彩”,一個是前期造假,一個是後期越做越漂亮。慢慢地,攝影師自己都迷失了。比如現在流行的一些寺院題材攝影照片,都是大家一哄而上、提着燈籠尋佛什麼的,都不真實。首先,拍攝一些原本不存在的東西,本身就有違佛教理念;其次,擺拍或者後期進行過大的改動,呈現出來的東西已經是美術作品,而不是攝影作品。
畫畫可以進行想象、創造,但是攝影不行。有時候聽到別人說我的照片跟畫出來的一樣,雖然對方是出於真心的誇獎,但我的內心還是會為攝影感到很悲哀。攝影不是畫畫,它是一個單獨的藝術門類。
攝影首先要做到真和實,然後才會出滿意的作品。我修圖一般是以原來的照片為準,基本原則是不改動畫面里的東西,且拍攝的必須是要真實發生中的事情。在原來的基礎上稍微加工一下,即便在傳統的暗房裡邊也是允許的,暗房也需要通過調試水溫,根據放大燈照射的時間來控制影調的深淺或者色彩,也有後期的剪裁,即二次構圖等等類似操作。
維繫攝影藝術的特性,我認為就是要堅持真實的原則。攝影師必須要有攝影專業精神,不能找時代進步、技術發展等各種各樣的理由去違背攝影的本質。攝影作品必須基於真實發生的事情,這是其區別於其他藝術種類的最大特性。
文/陳雅芳 張陳慧